中国文化避免人的物化
那么,中国人是否陷入同样危险?我们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?我认为,儒家文化,或者广而言之中国文化,提供了避免这一危险的出路。
前面讲西方文化之所以物化地理解人,本原在敬神、信神,相信人神两分,主客两分,从而仅从理智理解人。中国人敬天。在座各位只要略加反思、体贴,就可知道,天在自己心目中的重要意义。中国文化就起步于敬天的那一刻。我们大概可以说,人类文明其实就两种基本形态,也即中国文明和中国以外的文明。那么,中国文明的本原是什么?就是敬天;中国以外的文明,其本原都是信神。
我们要理解这两大类型的文明的差异,就要理解天和神之区别,说来话长,只是简单提示一下。在神教中,神造人,如果大家看英文本,用的是create或Make这样的词,神造人是物化的制造过程。但中国人讲,天地“生”人,具体表现为父母“生”人。中国人讲阴阳、天地和合而育万物,《周易·系辞》说:“天地絪缊,万物化醇。男女构精,万物化生。”。这就完全不一样。在西方文化中,有一个绝对的主体造人。我问一下大家:上帝是男性还是女性?没人知道,也许没有性别,但它是一个绝对的主体,造出了所有人。我们中国人则相信,一定是两个主体结合,并且一定是深度的融合,才生出一个人来。这两个原点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。
生,则所生者必然不同。天生人,天下万物必定各不相同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,物是物,人是人,人跟物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中国人严人、物之别,人跟物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。《尚书》说:“唯天地,万物父母;唯人,万物之灵。”孟子讲:“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”。人身上有一点点东西,把人和物彻底分开。那么,这个“几希”是什么?是人的心,孟子讲: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,人有恻隐之心,羞恶之心,是非之心,辞让之心。

《尚书正义》
这跟西方文化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西方文化基本上只讲人的mind,理智,中国讲人的心。心不是理智,或者说,心不仅仅是理智。人心当然包括理智,但还有其他,最起码的是,情。这是中国人对人的理解与西方人对人的理解的重大区别所在。我们读《理想国》,或者柏拉图其他著作,几乎看不到他讨论情感。情的问题始终不在他的视野之内,他所有的讨论都围绕理智展开。在基督教里也是如此,这就是区别所在。而中国人肯定了人之情。
大概是基于这一原因,中国人对于机器人世界的想象并不丰富。西方人相信,只要有理智,就可以是人。机器人有理智,所以他们对机器人有丰富的想象。但中国人打心眼里相信,机器不可能成为人,因为人有心,机器可以有理智,但没有心,机器怎么可以与人同日而语。
那么,中国人的这种平实想法,有没有道理?我觉得有。相对于西方,我们肯定了生命的完整。把人仅仅理解为具有理智,只要根据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可知道,这样的理解是偏颇的。当我在台上与大家沟通时,我没有办法把握大家的理智,但我通过大家的表情,可以看到大家情感的变化,我们可以有一个情感的互动。这不是理智决定的。
我想到今天上午刚看到的一则新闻。现在大家都在议论Master、AlphaGo的卓越能力,很多人就问百度,“你们在干吗呢?”百度有关部门回答说,我们在开发人脸识别技术,他们在某个娱乐节目上用“小度”识别人脸。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异?中国人爱“面子”,因为我们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我们重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。曾子说: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”:正容貌、正颜色、出辞气,彼此通过容貌、脸色展开情感交流。这也是生命的交流,而不是逻辑计算。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。
“人联网”、“心联网”
中国人在进入互联网世界时,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带入。据我观察,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可称为“人联网”,是人和人连接的网络;或者进一步说,是“心联网”,是人心与人心连接的网络。
2015年6月,马云到纽约经济俱乐部要对美国人发表演讲说:亚马逊是一个购物网站,人们知道要什么买什么;阿里巴巴则是一种生活方式,人们买到的是惊喜和体验。我可以换一种说法:亚马逊只是利用网络技术开了一家巨大的全球性超市,淘宝则创造和维系着一个复杂的社会。大家都会有体验,在淘宝上,店主和消费者之间会有密切的沟通,店主竭力通过各种方式加深与消费者的情感联系。他当然是要赚钱,但他的策略是动之以情。在这里,双方不仅是店家和消费者的关系,而是两个活泼泼的生命之间的连接和互动。
由此我们会看到,中国人对于人的理解跟西方人不一样,并把这样的理解带入互联网,或者我们可以说,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体认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,基于此构造出了中国式互联网生态。因此,中国互联网的界面、运作机理,跟西方的互联网有相当大的不同,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亚马逊和淘宝,微信和FB,微博与twitter。
显然,中西互联网世界背后的算法是不一样的,其区别在于,一个是围绕着mind展开的,一个是围绕着心展开的。在中国的互联网上,人仍然是完整的,绝不仅仅是个符号,人与人的连接也绝不仅仅是基于数学的算法。相反,在其中,人是以其心相联的,心之体为人性,心之用为人情,人借助网络构建人际关系,物联网则是人联网的一个载体。
西方的移动互联世界遭到人为切割。因为,人不是整体,而被看成诸多个别需求的集合,而且似乎相互没有关联。人有甲需求,就有一种甲工具。有乙需要,就发明乙工具。根本就没有互联网生态,也没有“世界”,只有相互隔绝的若干空间或领域。在互联网上,人的生命破碎了。这其实也是西方的传统:灵魂与肉体,世俗生活与属灵生活之两分。
相反,中国的互联网则是生态化的,因为中国企业家意识到了人的完整。人绝不仅仅只是消费者,或信息发布者,而是完整的人,尤其重要的是,人始终有情,相互全幅连接。故在中国,移动互联总是倾向于生态化、平台化,也即,尽可能把生命、生活全幅移入互联网世界,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完整交流,包括情感的交流。于是,人在互联网世界中仍然是人,而没有遭到技术的分割,在互联网世界中,人仍然是完整的。
总结一下:在中国,互联网是属人的互联网,是人联网、心联网。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,互联网始终主要是物联网,人也不过是其中一物而已。我认为,围绕心的互联,或者说心联网、人联网,能够让完整的人与其他完整的人相互连接的网络,可以避免人的物化。如果我们把人错误地理解为仅有理智,据此架构互联网,那么,人就会降格而物化,在这样的互联网中,人将遭到奴役。
互联网世界的秩序
我的第二个隐忧,涉及互联网世界的秩序问题。
我跟阿里研究院讨论5月份会议主题时,特意在“互联网”后面加了“秩序”二字。互联网世界必须有秩序,如果没有秩序,就无法存在。那么,怎么形成秩序?无非是两种办法:第一种是集中控制,比如说集权主义,由一个单一中心控制所有个体,这是可以形成秩序的,军队中,最典型,整齐划一,也是一种秩序。第二种是自组织,个体自我组织起来,相互协调。如此形成的秩序可称之为内生的,反过来,单一中心控制的秩序则是外生的。
据我的观察,总体来说,西方的互联网大概走了集中控制之路。这可能跟很多朋友的看法相背。因为我们都会说,西方人特别重视自由,强调个人主义,中国人则是集体主义的。我认为,这个所谓常识恰恰说反了。当然,这涉及一个漫长的讨论,此处省略。
人被控制之隐忧
上面已讨论了人的物化,由人的物化,可能带来互联网世界的一个可能危险,物控制人。比如,算法可能会建立起某种统治体系,算法的专制统治。作为物的算法支配人,在西方文化背景中,完全有可能。因为,西方现实就有所谓的法律的统治。大家仔细想一下,算法的统治和法律的统治,在逻辑上是不是一模一样?其构形是相同的。法律是什么?法律是外在的物,所有人服从此物,它规范、规定人应该这样、应该那样。这就是物对人的统治。它确实带来了秩序,但其中,人是自由的吗?我表示怀疑。
第二个危险就是具有霸权地位的企业或技术建立起对人的支配。这与前面的讨论有关,人遭到分割而不能保持完整,则人的身体分处在不同的体系中。在每一体系里,破碎的人都很难保持自己的完整和独立;当然,此时,人也会轻易地放弃这个部分,因为这反正不是我的全部。遭到分割的人很有可能在不同空间中被纳入单一中心控制的体系中,整体的后果是人遭到全盘控制。
我之所以有此隐忧,同样因为我所看到的西方精神之内在缺陷。读《理想国》、《利维坦》,深切感受到西方政治运作背后的深层次逻辑:一定要找一个主权者,一定要找一个至高无上的支配者;一神教则想象一个全知全能的唯一真神。唯有如此,人之间才有秩序,世界万物才有秩序。上帝、主权者是最大的主人,终级的主人,所有人都服从之,方才形成秩序。
这些阅读经验让我相信,西方文化中大概缺乏人群“自组织”的原型,他们无法想象人的自我组织。所以,当他们要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秩序时,总是借助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第三者,可能是上帝,也可能是政治主权者,也可能是神话般的人民,总之,西方人总是近乎本能地构造一个绝对的第三者,由其自上而下在分散的孤立的个体之间构造秩序。我担心,西方的互联网也会走上这条路。
中国互联网的基础:人生而就在与他人的连接中
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什么方案?让我们回溯到本原上。天生人,具体呈现为一个最基本的生物学事实: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,所以,每个人都生而在家中,或者更完整地说,每个人生而都在人伦中。什么是人伦?人伦就是人与人的连接,以个别的方式建立的亲密的连接。
我刚才讲到我对西方文化的担心,对西方互联网发展的担心。之所以担心,是因为,西方文化遮蔽了人获得其生命的基本事实,因而,人生而是孤立的,这些孤立的、被抛入世上的人,只能寻找一个第三者作为自己的主人,为自己构造秩序。我们在西方经典中可以读到两个非常有意思而重要的比喻。
第一个在《理想国》中,苏格拉底初步完成理想城邦构造后说,我们要告诉那些城邦的护卫者一个传说,并且一定要让他们相信这个传说,这就是所谓“高贵的谎言”:你们不是你们的父母所生,而是从土里长出来的,而且,你们出土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,拿着自己的武器。第二个在霍布斯的《论公民》中,而且那一章恰恰讨论家庭,但他拐了一个大弯。他说,我们要理解人的行为,还是要回到“自然状态”。什么是自然状态呢?在自然状态下,人像蘑菇一样从土来冒出来。
这两个比喻有类似之处,其用意都在强调,人不是父母所生;甚至这里都不说人从土里长出来、生出来,而说,人从土里“冒”出来的,冒出来的那一刻就是成年人。这两位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伟大人物,相隔近两千年,用了两个类似比喻,其目的何在?霍布斯的目的是说明,人是自然的,也即,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,因此需要一个主权者。柏拉图的目的是让城邦公民或城邦保卫者把自己完全献给城邦,献给国家,那他们就不能有私情,所以,他们必须相信自己不是父母所生。
以上两个比喻相得益彰,结局相同:被抛入的人绝对地服从主人,才有秩序。秩序是外生的,因为,人生而不连接,没有自组织能力,人间秩序只能由绝对的主人给予。
中国文化对于人的理解完全不同:人生而就在与他人的连接中。因为,人都是父母所生,所以我们一出生就在与人的相互联结中。事实上,我们之所以获得我们的生命,就是因为一对男女建立了亲密的连接。《孝经》说: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,这指出了人得到生命的基本事实,基于这一事实,人不仅生而相互连接,并且是有情的连接,心的连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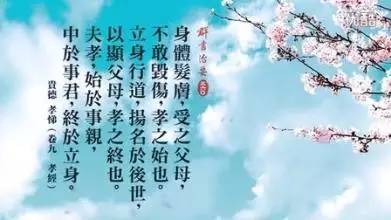
也就是说,中国人天生就在互联网中。互联网对中国人的生命而言,就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事实。我们就成长于其中,我们的生命就在互联之中。当然,这个相互连接的网络一开始是比较个别的,我们与父母、兄弟的连接是个别的。但在此个别的连接中,我们体认到连接的意义,学会连接的技艺。而我会走出家门,会和我的朋友、乡党、邻里、同僚、同学相连接。随着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,与人连接的网络也不断扩展。但连接的根本,则在父母生我的基本事实中,所以子游说:“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,孝悌者,其为仁之本与?”从父母开始,随着我的成长,我与人连接的范围越来越广泛,这就是我的成长过程。
由孝悌之情,扩充为普遍之仁,姜奇平先生从互联网视野对仁的内涵做了非常深入的阐发。仁就是人与人的连接,而且是充满情谊的连接,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。我们天生就在群中,我们生命的过程就是扩展群的过程,扩展群的种类或者规模,我们把自己置于各种各样交叠多样的群中,这是中国人生命之基本形态。
各位,这就是人的自组织。中国人天生就在自组织的组织中,并在生命过程中不断地丰富自组织的形态。在这样的自组织中,是没有什么第三者,更没有绝对的主权者。比如说在家里,你的爸爸还是妈妈是主权者?都不是。在家中,我们是在一种有情谊的关系中,我们相互体贴,相互为对方着想,协商共同的事务,当然,最为重要的是共同成长。中国人最不习惯于什么主权者。没有一个中国皇帝宣布自己是主权者,这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。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擅长于自组织的民族。
中国人把这样的生存经验或者说生命形态直接带入互联网,或者换句话说,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和用户,用自己的生存形态塑造了中国互联网的形态、生态。比如,微信在中国如此发达,人们建了一个又一个群,中国人寄存在各种各样的群中。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、期待塑造了中国式互联网生态契合了,反过来,互联网技术给人们过群的生活提供了便利。
总结:中国互联网与西方互联网的差异
很明显地,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生态存在巨大差异,这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可溯源于中西文化之不同。我们或许可以说,全球互联网发展之路可能有两条,中国的互联网之道,西方的互联网模式。而我认为,中国路径可能更好,因为它更有利于保障人的完整。这一点非常重要,在技术泛滥的时代,人如何保持自己的完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,我们只有保持完整,才可保持自主,才可保持人的尊严。基于中国文化的互联网生态,也许最有利于人保持自己的完整、自主、尊严。
当然,我绝不会说,今天的中国互联网生态就多好。中国人讲生生不息,我们永远到不了最好的状态。但如果我前面的讨论还有一点点道理的话,拿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互联网的文化自觉,或者说路的自觉,道的自觉。由此自觉,我们可以解释中国互联网为什么成功了;更重要的是,由此自觉,我们可以有意识地以中国文化塑造中国的互联网;更进一步,我们也许可以中国文化影响中国以外的互联网生态。
我相信,中国文化在整个世界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,在互联网时代,基于中国文化的更好的互联网生态,必然是影响力最大的。各位,让我们共同致力于中国互联网的道的自觉。
本文系由姚中秋教授在2017年1月7日网络智酷在涵芬楼书店主办的《儒家×互联网:互联网世界为什么需要儒家》沙龙上的发言整理而成,原文发表于网络智酷公众号。 |